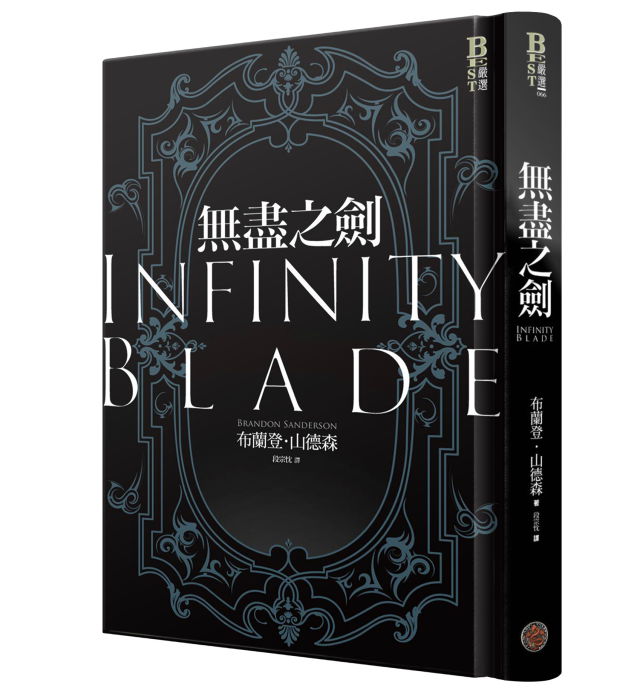神的死去對於德姆之喉的居民生活並沒有太大影響。事實上,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神明已經被殺了。
知道的人倒是趁虛而入。
「沒有什麼好擔心的。」威利斯站在臨時用兩輛板車搭建起來的講台上說道,身旁站著個戴銳—一種略具人形的壯碩生物。戴銳有很多種,這一個有著深紫色的皮膚,以及跟樹幹一樣粗壯的手臂。
「你們一直以來都繳稅給我,我也一直把你們的稅金上繳。」威利斯對聚集起來的人群說:「現在我會直接收取你們的稅金,成為你們的領主。對你們來說,有一個當地的領袖是件好事。」
「神王呢?」緊張的眾人之一大聲問道。好幾個世紀以來,德姆之喉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,為了達到徵稅標準,居民鎮日拚死拚活地工作,同時把所擁有的一切幾乎全交給稅收官。
「神王並未反對這個安排。」威利斯說。群眾裡有些人不滿地嘟囔,但是他們還能怎麼辦?
威利斯擁有戴銳跟士兵,據說他還有神王的祝福。
一名陌生人走到群眾邊緣。空氣很潮溼,聞起來有種礦石的氣味,德姆之喉建造在一個巨大的山洞裡,前方有個一百呎左右、像是咧嘴笑般的大開口,山洞頂上掛滿數千枚石筍,許多根粗到連三個男人合抱也抱不攏。
可是,大多巨大的石柱如今只剩下被砍剩的底座,洞穴頂上垂掛著上百條粗長的鐵鍊,一端拴死在岩石上,鎮上的男人每天都要順著鐵鍊爬上去,為神王挖掘珍貴金屬。
鎮裡的建築物每個月都會變換不同位置,避開有人工作的鐵鍊之處。即使如此,無論男女老幼,多數人還是都習慣戴上頭盔,以保護頭部不受到偶爾掉下來的碎石攻擊。
「為什麼是現在?我們以前都能自己挑選領袖,為什麼現在我們必須要有個領主?」一名比較勇敢的男人大喊問道。
「神王不需要向你們解釋原因!」威利斯大吼。他沒有戴頭盔,而是戴著公民帽跟穿著一套紫綠相間的絲絨華服。
鎮民安靜下來。違抗神王的旨意只能一死,大多數人甚至不敢多問。
陌生人繞著聚集的眾人外圍走,穿過用粗鐵環組成的垂鍊。有些人偷偷瞧他,想要一窺隱藏在兜帽下的臉孔。大多數人沒多理會他,認為他只是跟威利斯一同前來的人之一。他們把路讓開,讓他直直走向眾人的中心,威利斯還站在那裡繼續解釋他的新統治規則。
陌生人沒有推也沒有擠,人群沒有密集到需要他這麼做。他經過其中一條粗鐵鍊,停下腳步,伸出手撫摸著它。
那條鐵鍊中纏著藍色的緞帶,是上星期舉行慶典時留下來的。如今已經枯萎的花瓣仍然卡在一些縫隙跟角落裡,有些建築物甚至重新粉刷過,這一切都是為了每二十年才舉行一次的獻祭宴。
「所以,當然,我的權威不容質疑。」威利斯說道,並指向群眾最前面問問題的人。「你同意吧?」
「是……是的,大人。」男人縮肩回答。
「很好。來人,打他一頓之後,各就各位開始一天的工作吧。」
「可是,大人!我……」那人又回話。
「還爭辯。」威利斯俐落地一揮手。「你要付出代價,才會清楚記住你屬於誰。」
戴銳開始朝鎮民走去,那些不像人的怪物有不同的皮膚、形狀、顏色,有些有爪子,有些有燃燒的雙眼。牠們在人群中推擠,把年輕女孩從家人身邊拉走,包括剛才開口說話的男人的女兒。
「不要!」男人想把戴銳推開。「拜託你們,不要啊!」一個跟狼一樣頎長壯碩的戴銳上前,牠的皮膚上有堅硬的突起,臉部看起來像是受了燙傷般而發出嘶聲,然後舉起劍,朝那個人揮下。
噹的一聲響徹洞穴。
陌生人站在那裡,手伸得長長的,舉劍擋下了戴銳的攻擊。
鎮民、戴銳、威利斯彷彿都是第一次注意到陌生人的存在。周圍的人群立刻以他為中心,退成一個圈。
這時,他們看到了那把劍。
那把劍。兩側修長光滑,中間很明顯有三個孔……那是這塊大陸上每個小孩都必須學著認識的標誌。力量、權威、統治的標誌。
神王的武器。
那隻戴銳驚訝到呆站在那裡,等著陌生人一揮武器,從喉嚨刺穿了牠。陌生人眨眼間又抽出劍,向前猛撲,披風在他身後飛起,他抓住其中一條鐵鍊,熟練地盪起,盪向兩隻正將一名年輕女子拖向講台的戴銳。
那兩隻戴銳毫無反抗能力地倒下。牠們不是神王的守衛,只是普通的打手。陌生人放任牠們被自己湧出的鮮血嗆死。
威利斯開始大喊,想招來他的士兵,罵聲震天,詞出不窮,不斷指著陌生人叫嚷。然後,他突然安靜下來,連忙往後退,眼見陌生人已抓起一條鐵鍊,往前一衝一盪,重重落在板車上。紫色皮膚的戴銳拿著鈍頭的狼牙棒朝陌生人揮去,但是神王的武器──著名的
無盡之劍 ──在空中迅速一閃而過。
戴銳迷惘地看著被削斷的狼牙棒,棒頭悶聲落在板車上。片刻後,戴銳的屍體隨之落下。
威利斯想要從板車上跳逃,但是車身一震便讓他跪倒。他站起來時,發現劍尖已經抵在他的脖子上。
「叫他們退後。」陌生人輕柔地說。
「戴銳們!釋放所有人,往後退!往後退!」威利斯大喊。
陌生人的兜帽掉了下來,露出一頂遮住整張臉的銀色頭盔。他等怪物們退到縮成一團的鎮民外圍,然後舉起上面沾著死去怪物鮮血的利劍,指向通往城鎮之外的大開口。「出去。永遠不要回來。」
威利斯慌忙地照辦,從板車往下跳的時候整個人重重摔在地上,但立刻便全速跳起、衝出洞穴,戴銳們包圍著他一起奔逃。
洞穴陷入沉默。陌生人終於抬起手,拿下頭上的頭盔,露出滿頭大汗的褐金色頭髮,與一張年輕的臉龐。
賽瑞斯。祭禮。被送去等死的男人。
「我回來了。」他告訴所有人。
賽瑞斯往旁邊一撲。
從小開始,賽瑞斯就沒有盪鞦韆,沒有玩彈珠,甚至沒有吃過永莓派。他只有訓練。他也許沒有童年,也沒有少年期,但是他的失去是有所得的:反應神經。
賽瑞斯還沒反應過來為什麼要閃躲,身體已經開始行動,歪倒在地面後立刻縮成一團,讓自己盡量變小。他的腦子還沒分析出聽到什麼聲音,便已經完成這一系列動作。起因是後面傳來喀的一聲。
有東西劃過他的臉頰。白癡,他心想,居然在沒有戴頭盔時讓對方有可乘之機。他滾地後站起,背靠著神王寶座的高台,用它擋在自己跟窗戶之間。攻擊應該是從那個方向來的。他一手按著臉頰止血。
疼痛不算什麼。他利用一系列特殊的運動訓練自己忽略痛感,這個行為讓他在鎮裡的名聲不是太好。過程不愉快,但是很有效。
他完全靜止不動,貼著高台的岩石。那裡有幾名殺手?我需要武器。他很快便做出決定,放開了流血的臉頰,快步跑上通往寶座的台階,用沒有血的手抓起
無盡之劍 的劍柄,然後轉身繞到寶座旁邊打量他的敵人。
一個暗色的身影從靠近圓弧屋頂上方的窗戶垂了一條繩子下來。對方身形俐落、危險,穿著一件長到腳踝的黑色外套,下面是深褐色皮革,臉上罩著標準的面具,在賽瑞斯的理解中,這是神王屬下的象徵,也可能代表另外一名不朽。
對方從身側的劍鞘抽出一把細長的劍。賽瑞斯嘆口氣,伸展一下雙手,握住
無盡之劍 。他的盾牌放在一段距離外的桌子上,盔甲跟手套護甲也放在一起。他應該是來不及拿了,所以走下寶座高台,擺出防衛的姿勢,邀請對方進行堂堂正正的對決。為了以防萬一,治癒戒在他手指上閃閃發光。
他沒有把戒指用在受傷的臉頰上。那只是很單純的割傷,治癒有著可怕的代價。之前,他並不在乎,因為料定神王會殺了他。現在背後的代價讓他覺得很沉沉重。
他的對手端詳他片刻,然後舉起劍。開始了,賽瑞斯心想。對方卻放下劍,改從外套裡拿出一樣東西──一具精緻、危險的十字弓。
「地獄啊。」賽瑞斯立刻往旁邊一撲。對方發射出極度精準的一箭,短箭埋入賽瑞斯的大腿,正巧是盔甲金屬鐵片的縫隙。標準決鬥不是這個樣子。
賽瑞斯站了起來,身子一歪,痛得皺起眉頭。他從大腿拔起短箭,一面還要握著劍,一面提防對方的下一波攻擊。才剛拔起,就感覺大腿開始失去知覺。有毒。
地獄收了我吧!如今他沒有選擇。他在寶座高台旁尋求掩護,然後啟動戒指。
治癒立即生效。他感覺手指上一陣灼燒,魔法擴散,全身像是受到電擊,皮膚變得寒冷,如同整個人在冬天埋入一池冰水。
時間眨眼即過,他恢復過來時,疼痛已經消失,同樣在那眨眼的剎那,他的頭髮已經長到了肩膀,也長出了鬍子,指甲變長。
治癒戒以很變態的方式加速還原他的身體。雖然他復原得很快,傷口很快結痂,然後變成疤痕,但同時也讓他瞬間度過自然癒合需要的時間,立刻衰老。根據他的估算,每次使用戒指就要花上半年的壽命。
他舉手摸著剛長出來的鬍子,低頭從寶座高台的光滑大理石表面看著自己的倒影。他最痛恨使用治癒術。用得越多,他的五官就變得……越陌生。
他從大寶座的旁邊探出頭去。殺手正從寶座的另外一邊朝他潛伏而來,很顯然認為他正因為毒素攻擊而衰弱。當賽瑞斯從寶座後衝出去、跑向房間旁的牆邊時,對方發出很不像戴銳的叫聲。
殺手再次舉起十字弓,這次賽瑞斯已經有所準備。他低低彎下腰,往前一撲一滾,在桌子邊站起,拿起盾牌轉身舉起。
敵人立刻跑開,尋找掩護。賽瑞斯咬牙切齒。他在神王皇宮裡面對的每隻野獸,包括最汙穢的戴銳跟最原始的山怪都遵循古代決鬥精神。顯然他現在碰上完全不一樣的邪惡。
「所以……你還沒死嘛。」一個女性化的聲音從殺手逃走方向的柱子邊響起。她的聲音帶有淡淡的口音,賽瑞斯聽不出來是哪裡。她該發的音拖得過長,而且每個音節咬字都太用力。
賽瑞斯驚訝地眨眼,卻沒有回答。他繞回寶座高台,那裡很適合做為掩護。「這很尷尬。我要把那個商人的皮給扒了,他跟我保證這種藥是三息封喉。但從我射中你到現在,你呼吸的次數絕對遠超過三次。」隱藏起來的殺手的聲音在房間裡迴盪。
賽瑞斯來到高台底部。
「你會不會覺得有點累了?」那個聲音問。
「恐怕沒有。」賽瑞斯回喊。
「虛弱?頭暈?有點餓?」賽瑞斯呆了一下。「餓?」
「對啊。像是被人咬了?餓(注)不是那個意思嗎?」
「餓是想吃東西的意思。」他沒好氣地說。
「該死的。」柱子後面傳來一陣聲響,像是殺手在寫字。